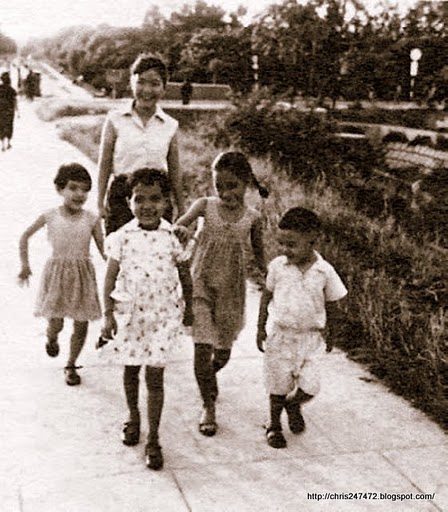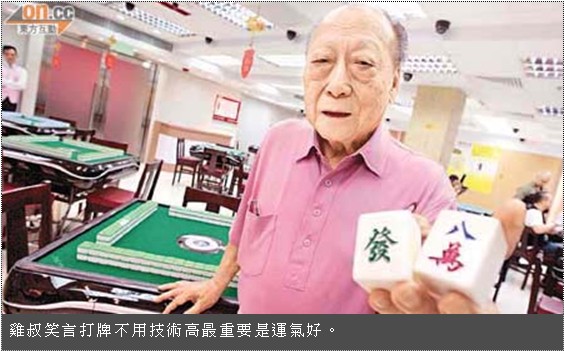要認識真正的香港,其實應該從舊區入手,比看歷史書更生活化和容易吸收。在眾多舊區中,油麻地的社區特色肯定是經歷多年風吹雨打的老舖和舊建築。正所謂「家有一老,如有一寶。」油麻地並不「麻麻地」,而是寶地。
始於小艇停泊處
早於1860年九龍半島割讓英國以前,油麻地一帶已有人聚居,天后廟內有一塊刻於清朝同治九年(1870年)的石碑,記載了當時該區稱「麻地」,只是一處供小艇停泊的淺灘。光緒元年(1875年),「麻地」改稱為「油麻地」,據說是因天后廟前的海灣廣場,為漁民曬晾船上麻纜而得名「麻地」,後來附近居民增多,有商店經營修補漁船所用的桐油和麻纜,因而被稱為「油麻地」。
油麻地經歷3次填海工程,第一次填海始於1875年,翌年油麻地獲重新規劃,開闢3條主要街道,即廟街、上海街和新填地街,並以現時天后廟為中心,建設低密度建築的市鎮中心,及後更夷平柯士甸道一帶山脈,把彌敦道延伸至油麻地。政府在1900至1904年進行第2次龐大的填海計劃,自新填地街填至渡船街,油麻地漸漸發展成九龍的商業中心,而上海街成為那裡最繁忙的街道。到了90年代初,九龍西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,商業中心的地位漸漸轉移至尖沙咀及旺角,油麻地的發展步伐卻放緩下來。
老店市集多籮籮
油麻地的歷史價值的可貴之處,不只是因為歷史建築的保存,更多的是因為建築內的老店依舊繼續經營,多年來的地道生活仍然得以體現出來。特色店如雕刻店、佛具店、刀具店等,在其他地區較少會於同一區出現。沿著上海街走一趟,幾乎可以一覽區內特色老店,得如茶樓、木器老字號永安號、永華臘味行、鏡明相架、陳枝記老刀莊、雙光電器等。除了上海街,廣東道與新填地街都有不少老舖,油麻地昔日的社會風貌,仍可從中略窺一二。
油麻地另一特色可說是市集和夜市特多,包括玉器市場和毗鄰的油麻地街市,以及3個露天市集,即新填地街(甘肅街、南京街交界)和廣東道露天市集(登打士街、碧街交界)及廟街夜市(廟街、街市街交界)。
當中最為吸引的有玉器市場,內裡攤檔有不少都是來自廣東道,後因政府規範而於1987年陸續遷入玉器市場。現時那裡分A、B兩區,合共約有300多個攤檔,售賣不同級別的玉器。內裡的另一特色便是「書信街」——有多間攤檔專為不懂寫字的人服務,包括寫書信和報稅,保留了昔日民間面貌。
歷史建築成焦點
由於昔日油麻地位處沿海,天后古廟是當地的標誌之一,亦是一級歷史建築物。逾百年歷史的天后古廟昔日臨近海邊,是漁民出海前必向馬祖祈求平安之處,後因填海工程而遷現址,現時與多株榕樹相伴——「榕樹頭」因而得名,那裡是街坊聚腳地,也是舉辦社區活動的熱點之一。
論歷史建築,不得不提法定古蹟的東華三院文物館。它前身是廣華醫院大堂,於1911年已經落成,文物館屬傳統的樑柱建築結構,結構柱以木建造,豎立在具雕飾的花崗石柱座上。牆身以青磚築砌。整幢文物館坐落於花崗石平台上,結構中西合璧,在1992年獲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。文物館內藏眾多珍貴歷史文物——歷史照片、檔案和文物,包括清光緒年間獲官員贈予的牌匾、1873年記載著東華服務單位每年收支情況等的《徵信錄》、1929年東華東院照片、50年代東華義莊的檔案和收據等,館藏豐富。
論人氣鼎盛,其中之一必定是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的油麻地果欄,據九龍果菜同業商會有限公司執行幹事莫澤強說,果欄的「繁忙時間」是由晚上至翌日早上,深夜燈火通明,人來人往。其實早在1913年已經落成的油麻地水果批發市場,最初不單售賣水果,還有蔬菜、雞、魚、米和乾貨等。之後,魚欄、菜欄、雞欄等在60、70年代相繼遷出,而大眾對水果的需求增加,水果經營規模逐漸擴大,全港約八成的鮮果都是從果欄批售。
摘自:文匯報2010年12月13日專題 ■文、攝:盧寶迪


 1908年豎立於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與佐敦道交界的紀念碑
1908年豎立於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與佐敦道交界的紀念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