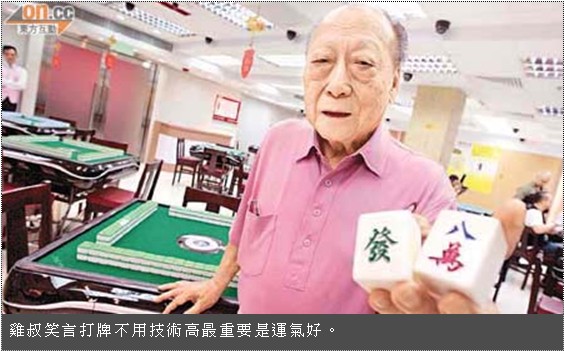『 真的勾起不少回憶,那時仲見到廣利理髮,曾有一段時期,其少東亦是我小學同學也。與再前一點的廣大理髮甚有渊源。
在廣大前一兩間舖,有花轎出租,出嫁的大紅花轎是也, 但從未見人結婚坐過花轎。而在租賃花轎的同時,亦有死人出殯用的「挺」出租,我只能說,但下知如何寫。出殯要「抬挺」,就像一輛轎,內裡放著死者遺照,幾個人抬住出遊,是為「抬挺」,以前死人出殯,有錢者會用車隊遊街,死人花牌,一個個用一些三輪單車撐住緩緩而行,有儀仗隊、樂隊及大批家屬跟著出遊,並會作出路祭,十分大陣仗。此外尚有一些如做戲看到的牌匾出租,有如狀元出巡時的肅靜、迴避木牌那樣,但這些物品叫什麽便不得而知了。
彌敦道乃大街,不可遊行,新填地街乃街市,攤販多,也不宜遊行。只有廟街、上海街及吳松街這幾條街會有此活動。』


真是觸景傷情,經街坊網友一提起便記得這列鋪,當中的確有間鋪頭如他所描述,但花轎我未見過,死人大燈籠上,斗大個藍色字則印象深刻。
小時候家住上海街舊樓,當時的上海街是一條主要街道,是富户辦喪事遊行所必經之路,他們不走彌敦道,更不行新填地街,童年時每次聽到遠遠傳來鼓樂聲,我跟弟弟便欣喜若狂地
最深刻的是鼓樂聲響與步操,俱整齊有序,通常是西樂先行,樂師身上都孭著樂器,就像檢閱儀仗隊般,一字排開,場面壯觀,非常震撼
當然,這些應該不是辦喪事的主軸,但小孩子盼望的就是這些有趣熱鬧場面,喪家的心情那會體會得到


舊樓沒升降機,樓梯又窄又直,有些是採用搭棚架方式把棺木卸下來,一些達到三四層樓的高度。




 ,當中來歷則頗堪玩味。
,當中來歷則頗堪玩味。


 ,但與我無關,那時我還是小童,只是助手一名而已
,但與我無關,那時我還是小童,只是助手一名而已